但长期以来,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特别是无限防卫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成为“僵尸”条文。“死者为大”“死了人就占理”,没理也集体闹访为有理,的确还是社会现实。不管是不是正当防卫,结果往往是“只要打死人就是故意杀人”“只要致人重伤就是故意伤害”。
但近年来,我国正当防卫似乎正在经历一个起死回生的演变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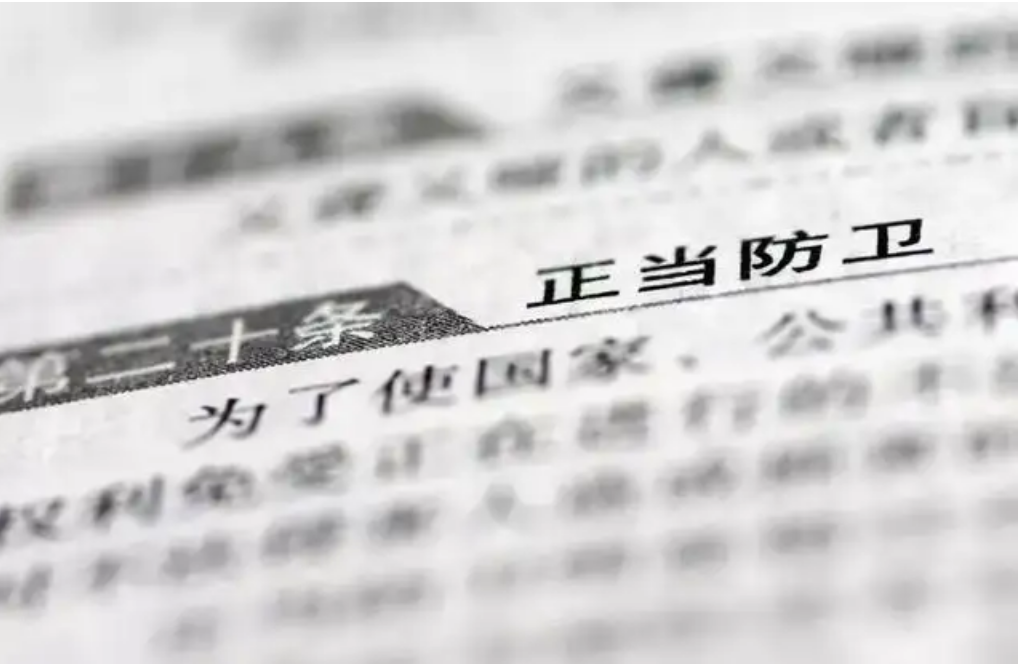
该案维持无罪后,该案原审检察院即三亚市城郊区人民检察院就多起故意伤害案以构成正当防卫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足见该案对司法实践的巨大影响。2020年9月,陈天杰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正当防卫典型案例。
本文想借“陈天杰正当防卫案”的是非对错,谈谈正当防卫制度为何长期“躺尸”,以及是否能起死回生。

被告人陈天杰,与妻子孙小娟在三亚工地当水泥工。某天晚饭后,夫妇两人做工时,三个年轻工友容浪、周世烈和纪亚练喝多了,言语调戏孙小娟,陈天杰赶过来后,这几人未作收敛,周世烈还用手摸了一下孙小娟的大腿。后陈天杰和这几人争吵起来,孙小娟摔倒在地,陈天杰蹲下扶孙小娟之际,容、周、纪三人对陈天杰拳打脚踢,周世烈捡了铁铲但被劝架工友抢下,纪亚练又从旁边找了根钢管重重地砸在陈天杰头上,幸好陈天杰带着安全帽只打到手臂上。陈天杰半蹲着护着孙小娟之际,顺手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单刃小刀,向身后乱挥、乱捅。容、周、纪三人受伤后逃走,容浪左股动静脉断裂,逃走后因失血过多休克而死,殁年19岁。周、纪二人也分别受轻伤、轻微伤。
但法院认为,陈天杰在被羞辱、被殴打后,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及其妻子的人身安全,防止对方不法侵害,陈天杰被动还击的行为不属于互殴,陈天杰不具有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
检察院认为,本案不存在可无限防卫的“行凶”行为。当天只是偶发斗殴;周世烈将铁铲扔掉,纪亚练只是把钢管打在陈天杰安全帽上,说明纪亚练等人主观上没有要致陈天杰于重伤、死亡的故意。
但法院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被害人一方所持的是钢管、铁铲,钢管击打的是陈天杰的头部,三人气势汹汹,陈天杰疲于应对、场面混乱,陈天杰无法判断是否能够免遭重大伤害,容浪等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行凶”,陈天杰可以进行无限防卫。
的确,假如构成无限防卫,其实不必再讨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但二审法院认为,这是依据第一款认定陈天杰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依据第三款认定陈天杰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此外,二审法院强调,陈天杰是半蹲着左手护住孙小娟右手持小刀进行防卫的,这种姿势不是一种主动攻击的姿势,而是一种被动防御的姿势。也就是说,陈天杰构成无限防卫,且陈天杰的防卫具有被动性和在必要限度内。
根据《刑法》第20条,只要是面临他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任何公民都有权实施正当防卫。只要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不构成防卫过当。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可无限防卫。我国“正当防卫”规定可以说简洁明了。
但也可以说过于简洁,导致司法实践普遍对正当防卫设置诸多限制性条件。但对这些限制性条件,因个人价值观、立场等不同,学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没有达成多少共识。具体案件中,就极度依赖办案人员对法律的理解。
比如陈天杰案,只就“不超过必要限度的手段、强度”这一问题,检察院和法院就在关于不法侵害所威胁的法益与侵害人死伤的结果怎么比较、判断基础事实、判断基准时点、以一般人还是当事人标准判断等具体问题,针锋相对,分歧巨大。
检察院似乎在认真回看“摄像头”,细细看了本案“黑色五分钟”每个人的细微动作,琢磨出来被害人一方捡了铁铲又扔了,拿着钢管只对着陈天杰安全帽来打,被害人仿佛只是闹着玩,陈天杰怎么能动刀子呢?
但法院似乎和陈天杰“一同蹲下”,从陈天杰当时的视角,三人凶神恶煞持械过来,还照着头部击打,被自己护着的妻子也可能随时被打,这是夫妇生死存亡的时刻,掏出小刀,可以吧?
在司法界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严格适用似乎是最方便、最安全的,因此检察院可以顶着舆论压力,对一审无罪判决坚持抗诉。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共识,想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一方也可能底气不足、束手束脚。还是陈天杰案,二审法院既然肯定本案构成无限防卫,则没有必要讨论防卫限度的问题,但二审判决还是从“陈天杰被动防御的姿势”、“陈天杰未追击逃跑被害人”等角度论证陈天杰的防卫还在必要限度内。相关用语甚至暗示一种道德判断,即面对可无限防卫的“行凶”场景,陈天杰一直是克制的、被动的,堪称是无瑕疵的无辜者。二审法官还一再强调陈天杰的行为是因为妻子被调戏,是为保护护着的妻子不被殴打,彰显陈天杰始终处于道德高地。但多余的话,强调的话,是不是也现实二审法官似乎还是对认定无限防卫稍有底气不足呢?这种底气不足,束手束脚,很好地反映了在没有共识现实下,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艰难。
在司法界并未就正当防卫诸多问题形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加之下文将提到的司法系统考评制度、维稳思维等现实阻力,即使有个别正面案例,甚至近几年这方面案例呈上升态势,但超前的正当防卫立法和滞后的正当防卫司法之间的偏差问题,恐怕短时间还很难改变。
根据刑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在处理正当防卫案件时,如果认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公安机关应当撤案、检察机关应当绝对不起诉、审判机关应当做出无罪判决,以上述方式结案并终止刑事诉讼程序。
但在现实中,以正当防卫为由终止刑事诉讼程序,往往并不容易。
如果案子从公安移送到检察院,被检察院撤案或者决定不起诉;或者已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被法院判决无罪;或者一审法院判决有罪,二审改判无罪,这些情况下,被下一程序改变处理结果的公安、检察院、法院相关人员当年的考评绩效都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因为意味着此前的办案机关把案子办错了。因此,公检法各方通常坚决维护自己的立场,比如陈天杰案的检方不顾舆论压力坚持抗诉;各方也尽量避免改变他方立场,以照顾他方面子和顾虑。
涉正当防卫案件往往有人伤亡,公安机关很少一开始就以正当防卫不立案或者撤案,一怕追责,二怕受害人闹事,宁愿先按故意伤害、杀人等刑事罪名继续推进刑事诉讼程序,让后面程序承担案件定性的责任和压力;但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程序越往后走,因为上述内部考评机制,改变案件性质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因此,除非公安机关一开始就认定正当防卫主动撤案,否则,案件可能一走到底,直到法院也很难反转。
正如上一部分所说,正当防卫制度本来就规定简单、适用复杂,司法人员之间有不同看法,十分正常。不能因意见不被下一程序采纳,就一概认定为错案并追责。否则办案人员骑虎难下,只能将错就错,人为增加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层层障碍。当然,这也不是正当防卫制度的独有问题,刑事诉讼无罪率非常低,恐怕也是这一司法困境的结果。
唐律记载,“为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依斗法。”也就是“打架无曲直”,都得处罚。司法实践习惯用“互殴”排除正当防卫制度,也算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了。一脉相承的是,重视社会秩序,而轻视公民防卫权。
但时代不是变了吗?
我国刑法第l条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规定为刑法的立法目的。一般来说,法治社会,只有国家权力机关才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主体,因此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均交给国家权力机关。但在例外情况下,也就是国家权力机关来不及阻止现行犯罪、救济公民的时候,公民例外有权利使用暴力维护自身及其他受侵害公民利益,这是公民的应有权利,法律确立正当防卫制度就是从法律上对这一公民防卫权的认可。
可能长期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惯性,司法界人士似乎更多认为自由是容易失控的、失序的,为维护抽象的或具体的公共秩序,也可以说是为了维稳,更倾向于限制适用公民防卫权。尤其涉正当防卫案件往往存在人员伤亡,不追究防卫人责任,被害人往往会无休止地到司法机关纠缠、上访、举报,其中不乏过激手段、媒体扩大、扰乱办公秩序等现象。为了避免维稳压力,尤其有些地区还以涉讼上访率作为维稳的指标,司法机关认定正当防卫的动机更低、顾虑更多了。
但在公民因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造成侵害人的伤亡结果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出于各种原因不认定防卫性质,不仅没有公正处理案件,也切实损害和不尊重公民的防卫权。
从维稳走向维权,需要司法人员对公民防卫权有更多的尊重;只有转换观念,才能就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达成更多共识,才能更好地正确应对诸多外在办案压力。
近年来,一些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经过媒体曝光以后,社会舆论普遍同情防卫人。但公众意见未必能得到司法机关的正视。比如陈天杰案,即使在舆论压力下,检方依然坚持起诉、抗诉。
法律人似乎很喜欢“法律思维”、“法律共同体”之类的话语,仿佛不应使法律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感觉相一致,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和大众意见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但民众朴素的是非观背后,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伦理道德,是“心里那杆秤”,这种朴素的法感情不应被少数精英无视,更不应被嘲笑。比如是互殴还是正当防卫,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实质是“不正对不正”,还是“正对不正”的是非判断。假如司法机关的是非判断,总是与大众的是非判断截然相反,长此以往,大众是信仰心中道德,还是信仰不符合道德的刑法?
就陈天杰案而言,假如再有人的新婚妻子被人调戏,是应该逃跑还是应该抗争?
起码法院的无罪判决,可以让大众对这一基本问题,有一个基本安心的判断。
正如苏力教授曾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往往依据一种所谓的普适的原则来说话,我们往往并不真正理解基层社会的普通人究竟需要些什么。”涉正当防卫制度案件,适当听听大众的意见,说不定可为定案找杆称。
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的全面激活,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虽道阻且长,法律人一起努力吧。
